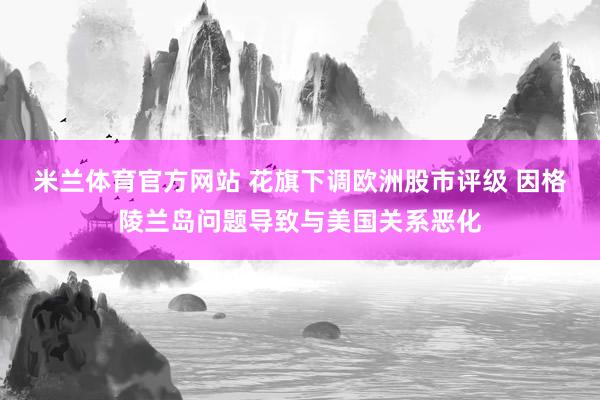楔子
有些爱,以占有为名,行绑架之实。
当你试图活成自己的模样时,最先举起刀剑的,往往是最该祝福你的人。
婚礼前一小时,家族群里的每一条语音,都像一把精准的刻刀,将我雕琢成他们满意的作品。
而我的母亲,是那位最虔诚的雕刻师。
直到那条五十九秒的语音弹出,我终于听见了刀刃破空的声音。
01
化妆镜里,我穿着定制婚纱,头纱垂在肩侧。
距离婚礼开始还有六十分钟。
化妆师小雅正在为我调整最后一缕发丝,她的手指很轻,像是怕碰碎什么。手机在梳妆台上震动第七次时,她终于忍不住低声提醒:“薇薇姐,要不……先看看?”
屏幕上是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微信群——“家和万事兴(27)”。
这个群里,有我的父母、七大姑八大姨、舅舅舅妈,以及所有能扯上血缘关系的亲戚。二十七个人,二十七个审判官。
最后一条消息,是母亲发的语音。
五十九秒。
在这个家里,母亲说话从来简明扼要。超过三十秒的语音,通常意味着两件事:要么是极致的赞美,要么是彻底的宣判。
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,婚纱的缎面袖口在酒店水晶灯下泛着冷光。
“听听吧。”我的伴娘,也是十年好友苏晴,把手轻轻搭在我肩上,“反正,该来的总会来。”
她比我更了解我的家庭。
我点开那条语音。
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流淌出来,平静,甚至算得上温和:
“薇薇,各位亲戚,趁现在人齐,我说几句。今天这个婚礼,我们林家等了二十八年。薇薇从小懂事,就是有时候太有主意。不过女孩子嘛,终究要回归家庭。小陈家里条件是好,但咱们也不差,该有的礼数不能少。待会儿婚礼上,有几个事我得先跟大家通个气——”
她的声音在这里顿了一下,那是她准备抛出重要事项前的习惯性停顿。
“第一,改口费。小陈父母之前说给一万零一,取‘万里挑一’的好意头。但我打听过了,他们给前儿媳是这个数,给咱们薇薇不能一样。我让你爸准备了张卡,里面是六万六,待会儿敬茶时你直接递给小陈,让他当众补上差额。咱们林家的女儿,不能比别人差。”
化妆间里的空气凝固了三分。
小雅的手停在半空,睫毛夹闪着金属的冷光。
语音继续:
“第二,婚宴致辞。主婚人是你大舅,但他普通话不太标准。我写了份稿子,已经发给他了。里面要重点提三件事:你考上公务员是靠家里托的关系,你现在的工作是你表叔帮忙安排的,还有,这套婚房的首付,咱们家出了四十万。”
苏晴倒抽一口冷气。
而我,竟然在笑。
镜子里的新娘,唇角上扬,眼睛却一片冰冷。
语音到了最关键的部分:
“第三,关于婚后。小陈之前说想丁克,这绝对不行。我们林家五代单传,到你这一代就你一个女儿,你必须生两个孩子,第一个跟我们家姓。这事我已经跟亲家公亲家母通过气,他们答应了。待会儿婚礼上,司仪会安排一个环节,让小陈当众做出承诺。”
五十九秒的语音,播完了。
化妆间里死一般的寂静。
然后,手机开始疯狂震动。
二姨:“大姐想得周到!支持!”
小舅:“还是大姐有远见,不能让他们家看轻了咱薇薇。”
三姑:“生两个好,一个姓陈一个姓林,公平!”
表嫂:“薇薇真有福气,有这么为你着想的妈妈。”
一条条文字冒出来,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合唱。
所有人都在赞美母亲的“深谋远虑”,赞美她的“爱女心切”。
没有一个人问:林薇,你想要这样吗?
哦,不对。
有一个人问了。
父亲在群里发了个大拇指的表情,然后单独@我:“薇薇,听你妈的。她都是为了你好。”
看,多么完美的闭环。
母亲制定规则,亲戚拥护规则,父亲维护规则。
而我,只需要执行规则。
“薇薇姐……”小雅的声音在发抖,“还有五十分钟,仪式就……”
苏晴一把抓过我的手机,手指飞快地打字。
我知道她想干什么——她想在群里反驳,想为我说话。
我按住了她的手。
“没用的。”我的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,“这个群存在七年了。七年来,我反驳过二十三次。你猜结果怎么样?”
苏晴看着我,眼圈慢慢红了。
她知道结果。
每一次反驳,都会换来母亲三天的冷战,父亲一个星期的唉声叹气,以及所有亲戚轮番的“劝导”。
“你妈不容易。”
“她都是为你好。”
“等你当了妈就明白了。”
这些句子,我听了二十八年。
手机又震了一下。
这次是私聊。
母亲发来的:“薇薇,都看到了吧?照做。别让妈在亲戚面前丢脸。”
紧接着,又是一条:“对了,你婚纱胸口开得太低了,我让化妆师给你别朵花遮一下。女孩子要端庄。”
我抬起头,看向镜子。
这件婚纱,是我攒了八个月工资买的。试穿那天,陈诺眼睛亮得像盛满了星星。他说:“薇薇,你美得让我不敢呼吸。”
而现在,母亲要在这片白色之上,别一朵俗气的绢花。
手机还在震。
表妹私聊我:“姐,姨妈也是为了你着想。陈家那么有钱,咱们要不把规矩做足,以后你要受气的。”
堂弟也发来消息:“姐,男人结婚前什么都会答应,结婚后就变了。姨妈这是在帮你争取保障。”
看,每个人都是为我好。
每个人,都在用他们的方式,“爱”我。
我慢慢站起来,婚纱的裙摆在地上铺开,像一朵盛开到极致、即将凋谢的花。
“小雅,”我说,“头纱拆了吧。”
“什么?”
“拆了。”我重复,“还有,这身婚纱,帮我脱下来。”
化妆间里,两个女孩惊恐地看着我。
苏晴第一个反应过来:“薇薇,你想清楚,婚礼马上就要——”
“正因为它马上就要开始了。”我转过身,看着镜子里那个妆容精致、穿着华丽嫁衣的女人,“所以,我必须现在做决定。”
“是穿着这身囚服,走进他们为我设计的余生。”
“还是……”
我伸手,抓住头纱的边缘。
薄如蝉翼的纱,握在手里却重若千钧。
02
头纱被扯下的瞬间,发出一声轻微的撕裂声。
那声音很轻,轻到几乎被空调的出风声掩盖。但在我听来,却像是某种契约被硬生生撕开的脆响。
“薇薇姐,你别冲动!”小雅扑过来想抓住我的手,睫毛膏在她年轻的脸颊上晕开黑色的泪痕,“还有四十五分钟,陈诺哥还在外面等着,宾客都到齐了,这、这不能开玩笑……”
苏晴没有说话。
她只是看着我,看了整整十秒钟。然后,她走到化妆间的门边,反手锁上了门。
“小雅,”苏晴的声音异常平静,“帮薇薇把婚纱脱下来。小心点,别扯坏了,要退的。”
“晴姐!你怎么也——”
“二十八年了。”苏晴打断她,走到我身后,开始解我背后的绑带,“林薇当了二十八年的‘好女儿’。就让她做一次自己,不行吗?”
绑带一层层松开,那些为了穿上这件婚纱而屏住的呼吸,此刻终于可以大口喘息。
婚纱从肩头滑落,堆在脚边,像一团失去生命的云。
我穿着简单的吊带衬裙,走到衣柜前,拿出原本准备婚后蜜月旅行穿的便服——白色棉T恤,蓝色牛仔裤,一双帆布鞋。
“薇薇,”苏晴的声音在身后响起,“你想好了?这一走,可就回不了头了。”
镜子里的我,正在擦掉化妆师精心描绘了两个小时的新娘妆。
卸妆棉划过脸颊,带走粉底、眼影、腮红,露出我本来的肤色。有点暗沉,眼下一圈淡淡的青黑,那是连续一个月加班筹备婚礼的痕迹。
“七年了,苏晴。”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也看着镜子里的她,“从大学毕业那天起,我妈就在为我规划人生。考公务员,托关系进现在的单位,和‘合适’的人相亲,在‘合适’的年龄结婚。”
“陈诺是第七个相亲对象。前六个,有的因为‘身高不到一米八’被否,有的因为‘父母是普通工人’被否,有的因为‘不会来事’被否。陈诺过关,不是因为他多好,而是因为他每一项都踩在我妈的标准线上:父母经商,身高一八五,本地户口,有房有车,性格温和——翻译过来就是,好控制。”
苏晴走到我身边,拿起另一片卸妆棉,帮我擦掉脖颈上的粉底。
“那你爱他吗?”她问得直接。
我手上的动作顿了顿。
爱吗?
陈诺会在我加班时送宵夜,会记得我生理期的日子,会在过马路时下意识把我护在里侧。他温柔,体贴,情绪稳定,是所有人口中的“理想结婚对象”。
可我们约会时,聊得最多的是房价、学区政策、未来孩子的教育规划。
我们很少聊梦想。因为我的梦想——开一家独立书店,在每周日办读书会——在他听来是“不切实际的小资情调”。
我们更少聊痛苦。因为我每次提起工作中的委屈,他都会说:“忍忍就过去了,体制内稳定,多少人想进都进不来。”
“他爱我吗?”我把问题抛回去。
苏晴笑了,笑容里有些苦涩:“他爱的是‘林薇’——公务员,家境清白,性格温顺,适合娶回家当妻子的林薇。至于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,他可能从来没想过要了解。”
是啊。
就像我妈,爱的是“女儿”这个身份,而不是林薇这个人。
手机又开始震动。
这次是陈诺。
我接起来,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焦急:“薇薇,你妈刚来找我,给了我一张卡,说什么改口费……这怎么回事?还有,司仪说流程有变动,要加个环节,让我当众承诺生孩子的事。这太突然了,你怎么没提前跟我说?”
“陈诺,”我打断他,“如果我现在告诉你,我不想生孩子,不想让我的孩子姓林,不想在婚礼上被你当成展示品一样承诺这些,你会怎么办?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沉默了三秒,在婚礼前四十分钟,这三秒长得像一个世纪。
“薇薇,”他终于开口,声音里带着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,“都快结婚了,你说这些干什么?你妈也是为咱们好,有什么问题婚后慢慢商量不行吗?”
“婚后?”我笑了,“婚后,这些‘为咱们好’就会变成‘为这个家好’,变成‘为孩子好’。然后我就该辞掉工作,全职带孩子,因为‘女人要以家庭为重’。等孩子大了,我又该去求人找份清闲的工作,因为‘不能和社会脱节’。等我老了,我这一生就会变成一句总结:‘她是个好妻子,好母亲,好女儿’。”
“陈诺,”我轻声问,“那我呢?林薇这个人,她的人生呢?”
电话那端传来司仪催促的声音,还有宾客的喧哗。
陈诺压低声音:“薇薇,别闹了。这么多亲戚朋友都看着呢,milan有什么事婚礼结束再说。你先把妆化好,仪式马上开始了。”
“陈诺,”我叫他的名字,最后一次,“我给你两个选择。第一,你现在去告诉司仪,取消所有临时添加的环节,改口费按原计划,婚后生活我们两个人自己决定。第二——”
“薇薇!”他急了,“你这不是让我难做吗?你妈、你爸、所有亲戚都在,我这时候去说这些,他们怎么看我?婚礼结束再说不行吗?”
“好。”我点点头,虽然他看不见,“我知道你的答案了。”
挂断电话,关机。
动作一气呵成。
“决定了?”苏晴问。
“决定了。”我穿上帆布鞋,系好鞋带。
小雅在一旁小声啜泣,不知是为这场破碎的婚礼,还是为那个曾经也幻想过婚纱与爱情的自已。
我从随身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信封——里面装着我的身份证、储蓄卡、一张三天后飞往大理的机票,还有一封昨晚写好的信。
信是写给陈诺的。
我把它放在梳妆台上,用那顶被我扯下的头纱压住。
“小雅,”我转身看着这个今天才第二次见面的化妆师,“婚纱和首饰都在这里,退租的票据在包里,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。尾款我会微信转你。”
“晴,”我拥抱苏晴,在她耳边说,“帮我拖三十分钟。三十分钟后,如果有人问我去哪,就说我去追求我的人生了。”
“你要去哪?”
“不知道。”我诚实地说,“但我知道我不想留在哪。”
打开化妆间的门,走廊里铺着红毯,一直延伸到婚礼大厅。厅内传来悠扬的乐曲,司仪正在做最后的暖场。
我朝反方向的消防通道走去。
高跟鞋踩在地毯上,寂静无声。
手机在口袋里震动——这次是父亲的电话。我按掉,他再打,我再按掉。
第三次,他发来短信:“薇薇,接电话!你妈气哭了!有什么不能好好说!”
我没有回复,只是加快了脚步。
推开沉重的消防门,楼梯间里灯光昏暗,空气中有灰尘的味道。
我一级一级往下走,婚纱的裙撑还攥在手里,像个可笑的、巨大的白色泡沫。
走到三楼时,上面传来嘈杂的人声和脚步声。
“薇薇!林薇!”是母亲的声音,尖利,颤抖,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恐慌。
我没有回头。
消防通道的门在一楼被锁住了。我拐进走廊,穿过堆满桌椅的储藏室,从酒店后厨的后门溜了出去。
六月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,我眯起眼睛。
身上还穿着酒店的白色拖鞋,脚上沾着厨房的油污。手里的婚纱裙撑不知该扔去哪,最后我把它塞进了后巷的垃圾桶。
掏出手机,开机,叫车。
等待的间隙,家族群又弹出了几十条消息。
不用看我也知道内容。
无非是——
“这孩子太不懂事了!”
“白养她这么大!”
“快把她找回来!”
“亲戚们都看着呢,这脸往哪搁!”
我笑了笑,点开母亲的微信对话框。
打字,删除,再打字。
最后,我只发了一句话:
“妈,我去做林薇了。您就当我这个女儿,白养了吧。”
发送,拉黑。
车子到了,一辆白色的网约车。
司机摇下车窗,疑惑地看着我这个穿着T恤牛仔裤、却一脸新娘妆残痕的女人。
“去机场。”我拉开车门。
车子驶离酒店后门时,我回头看了一眼。
那栋华丽的建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像一座精心打造的黄金牢笼。
而我现在,越狱了。
手机在副驾驶座上震动,屏幕上闪烁着“爸爸”两个字。
我没有接。
直到它第三次响起,我才拿起来,按了接听键。
“林薇!”父亲的声音是暴怒的,那种被挑战了权威的、恼羞成怒的暴怒,“你立刻给我回来!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!你妈气得昏过去了!所有亲戚都在看笑话!我们林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!”
我安静地听着,等他一口气吼完,才轻声问:
“爸,我今年二十八岁了。你还记得我喜欢吃什么,讨厌吃什么吗?”
他愣了一下,显然没料到我会问这个。
“你、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!赶紧回来!”
“我喜欢吃辣,讨厌吃香菜。我芒果过敏,但喜欢吃芒果味的冰淇淋。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加缪,高中时在作文里写过,你说我不务正业。我想学中文,你非让我报会计,说好找工作。”
我一字一句地说,语速很慢,像是怕他听不清。
“我谈过三次恋爱。第一次是大二,对方是文学社的学长,你们说他家是农村的,没前途,逼我分手。第二次是工作后,同事,你们嫌他个子矮。第三次,是陈诺。你们满意了,可我不满意。”
“爸,”我的声音开始发抖,但我努力让它平稳,“这二十八年,我一直在做你们的女儿,做亲戚们口中的‘好孩子’,做社会要求的‘适婚女性’。今天,就今天,让我做一次林薇,行吗?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长久的沉默。
然后,我听见了哽咽声。
不是母亲的,是父亲的。
那个在我记忆里永远严肃、永远正确的男人,在电话那头,哭了。
“薇薇……”他的声音破碎不堪,“爸爸只是……只是怕你过得不好……”
“可我从来没好过。”我说,“在你们的爱里,我窒息了二十八年。”
挂断电话,关机。
车窗外的城市在倒退,高楼,街道,行人,红绿灯。
一切都那么熟悉,又那么陌生。
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,小心翼翼地问:“姑娘,逃婚啊?”
我愣了愣,然后笑了:“是啊,逃婚。”
“逃得好。”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,她咧开嘴笑,露出有点黄的牙齿,“我当年就是没逃成,现在后悔半辈子。”
“是吗?”
“可不是嘛。”大姐打了转向灯,车子拐上机场高速,“我那老公,是我妈挑的。说老实,可靠。是老实,老实地出轨,老实地把家里钱都赌光。我忍了二十年,去年离了。我妈到现在还说,是我没本事,拴不住男人。”
她从后视镜里看我,眼神里有种过来人的通透:“姑娘,能逃的时候,赶紧逃。等人进了笼子,翅膀就硬不起来了。”
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,突然问:“大姐,如果你女儿逃婚,你会怎么样?”
“我?”大姐哈哈笑起来,“我给她买机票,再塞点钱,告诉她,跑得越远越好,别回头!”
我们都笑了。
笑着笑着,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03
机场大厅里,人来人往。
我站在巨大的航班显示屏下,看着那些陌生的地名:昆明、成都、西安、乌鲁木齐、拉萨……
每一个地名,都代表一种可能性。
一个不需要解释“我为什么是我”的可能性。
距离起飞还有两个半小时。我在便利店买了瓶水,找了个角落坐下,打开手机。
微信有99+条未读,家族群被我屏蔽了,但私聊框还在不断弹出。
表妹:“姐,你太酷了!虽然我妈骂了你一晚上,但我觉得你做得对!等我长大了也要像你这样!”
这条让我笑了。
堂哥:“薇薇,哥支持你。但妈那边你得哄哄,她心脏不好。”
这条让我叹了口气。
舅舅:“你太不懂事了!你妈养你这么大,你就这样回报她?赶紧回来道歉!”
这条让我直接划掉。
然后,我看见了陈诺的消息。
三十七条。
从最开始的焦急困惑,到中间的愤怒指责,再到最后的哀求挽留。
最后一条是二十分钟前发的:
“薇薇,我错了。我不该只听你妈的,不该不考虑你的感受。你回来,我们重新办婚礼,就按你想要的来,好吗?”
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。
如果是一个月前,一周前,甚至昨天收到这条消息,我可能会心软,可能会回去,可能会告诉自己“婚姻就是这样,要互相妥协”。
但现在是现在。
是我穿着T恤牛仔裤坐在机场,妆花了,头发乱了,但心脏在胸膛里跳得前所未有的有力的现在。
我回复:“陈诺,谢谢你爱我。但我想,你爱的可能是那个‘适合结婚的林薇’,而不是真正的我。而真正的我,连我自己都才刚刚认识。对不起,耽误你这么久。祝你找到一个,你真正爱的人。”
发送,拉黑。
做完这一切,我长舒一口气,靠在冰冷的机场座椅上。
手机又震了。
这次是苏晴。
“安全到达?”
“在机场了。那边怎么样?”
“还能怎么样,兵荒马乱。你妈真昏过去了,不过很快就醒了,现在在休息室哭。你爸在跟所有亲戚道歉。陈诺和他父母脸都是绿的,司仪在拼命圆场,说新娘突发急病送医了,婚礼延期。”
我几乎能想象那个画面。
“晴,谢谢你。”
“谢什么,我早就想看你这么干了。对了,有个事得告诉你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你走之后,你妈翻了你留在化妆间的包,找到了那张机票。她现在已经知道你飞大理了。以她的性格,可能会追过去。”
我握紧了手机。
果然。
二十八年的控制,不会因为一场逃婚就结束。
“还有,”苏晴顿了顿,“你妈在家族群发了条长语音,说你被外面的男人骗了,说你有婚前焦虑症,说你精神不正常需要看医生。总之,她把你逃婚的原因,归咎于一切,除了她自己。”
我笑了,这次是真的笑出声。
“随她吧。对了,帮我个忙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我公寓的钥匙你有,帮我收拾点行李寄到大理。地址我微信发你。其他的,该扔扔,该送人送人。”
“包括那件婚纱?”
“尤其是那件婚纱。”
挂断电话,我看着机场窗外的跑道。
飞机在起起落落,每一架都载着去往不同人生的人们。
而我,即将登上其中一架,飞向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确定的未来。
登机口开始排队时,家族群又弹出一条@所有人的消息。
这次是父亲发的:
{jz:field.toptypename/}“今天的事,是林家没教育好女儿,给各位亲友添麻烦了。薇薇身体不适,婚礼延期,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再次向大家道歉。”
典型的林家作风。
把问题归结为“身体不适”,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,维持表面和平。
我没有回复,只是在关机前,给父亲发了最后一条微信:
“爸,我身体很好,从未这样好过。另外,婚礼不会延期,因为它永远不会举行了。对不起,以这种方式让你们难堪。但如果不这样,我的一生都会难堪。保重身体,勿找。”
点击发送,关机。
飞机冲上云霄时,我从舷窗往下看。
那座我生活了二十八年的城市,在脚下渐渐变小,变成灯火组成的棋盘,最后被云层彻底吞没。
再见,林薇。
再见,那个永远听话、永远懂事、永远在满足他人期待的“好女儿”。
从今天起,我要去认识那个喜欢吃辣、讨厌香菜、芒果过敏但爱芒果冰淇淋、喜欢加缪、想开书店的林薇了。
哪怕要用一生。